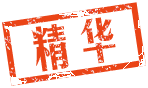本帖最后由 嵛少爷 于 2021-3-30 18:26 编辑
刚写完第一篇,先发一下看看,我尽量写得详细一点,尤其是音乐方面,我会配上图,希望便于阅读
第一章
与众不同的人文主义之美 浅谈巴洛克时期的艺术风貌
开篇,我想从西方艺术史上一个非常重要和辉煌的时期跟大家聊起,那就是巴洛克时期。 谈到巴洛克,我们就不得不先从它前面的“文艺复兴”开始讲起。 中世纪晚期的欧洲(十四世纪),封建的骑士制度和神圣罗马帝国的权威开始走向衰落,经院哲学的地位也逐渐产生了动摇,社会和经济生活的中心渐渐从封建城堡转向了手工业不断崛起的城市。文艺复兴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兴起的(从大约一三零零年到一六五零年)。“文艺复兴”一词是法文“重生”的意思,由历史学家朱尔·米什莱(Jules Michelet)率先提出。 作为欧洲文化摇篮的古希腊文明与后来的古罗马文明一起将欧洲古代文化推向了黄金时期。但事实上,庞大的古罗马帝国虽然继承了古希腊文化,并以更加辉煌的态势继续向前推进着。但这种看似繁荣发展的背后却早已丢失了古希腊文化中的精髓,而使这种发展几乎流于形式。以音乐为例,古罗马音乐继承了古希腊的许多特点,其音乐的高度发展亦不压于古希腊,但希腊音乐中的那种高尚与纯真,那种能净化心灵的功能(教化功能)却再也看不到了。古罗马的音乐更像是纯粹性的娱乐,那些复杂、炫技,注重享乐的音乐常常成为当下生活的主流。而文艺复兴时期的进步思想家们想要“重生”的,也正是那些失去已久的古希腊哲学与古代艺术的崇高价值。他们抱着“人文主义”的情怀,否定着被中世纪神学所笼罩的一切。由此可见,文艺复兴在思想上是一种以展现人文精神,表现人性的一种思潮。它在艺术的表现形式上,当然是竭力效仿古希腊那种简朴庄重,和谐稳定的模式。 欧式艺术史上的“巴洛克”时期,指的正是文艺复兴晚期的一百五十年间(约一六零零年至一七五零年)。 “巴洛克”一词的来源有两种说辞,第一种认为法语词“Baroque”来源于葡萄牙语“Barroco”,意思为“不规则的珍珠”。另一种则是学者卢梭提出的,这个词实际上源自意大利语,是一个形容词,用来指逻辑学三段论中的一种牵强附会的方式。无论是以上哪种说法皆不能否认的是,“巴洛克”具有“畸形、不自然”的意思,这让我不禁想起了曾经在乌克兰生活的一段往事。有一次,我家养的一只英短猫好像后腿出现了问题,于是就带去医院做检查。后来,医生在给我叙述病情时就用到了“Baroque”这个词。虽然我从来没有接触过这个词,但却能一下理解医生的意思——猫的后腿有畸变。而艺术史家们之所以用“畸形”来概括文艺复兴晚期的艺术,正是因为那个时期在艺术形式上有点偏离了古文化中严肃、含蓄、均衡的特点,在当时的人们眼中已经走上了过度极端化的一面。 现在,就让我们来简单谈谈巴洛克时期在视觉艺术方面的独特之处吧。 首先,它继承了文艺复兴所体现出来的人文主义精神,艺术创作中虽然不乏有很多宗教题材的作品,但却处处闪耀着现实的“人性”。 这幅名为《圣母离世》的油画作品出自意大利天赋异禀的画家卡拉瓦乔之手,是画家受圣玛利亚德拉斯卡拉教堂之托而创作的一幅作品,但最后却被教堂拒收了,现存于巴黎卢浮宫中。让我们来看看,画面中被众人环绕着,脸色苍白的红袍女子就是卡拉瓦乔笔下已经离世的圣母了。 圣母玛利亚作为耶稣之母,在西方宗教中有着非凡的地位和意义,尤其在艺术创作中更是“神圣崇高”一词的具象化。不同时代、不同作曲家谱写的《圣母颂》都充满着那么热烈的谦卑与虔诚,而画家笔下的圣母形象更是圣光注照,泽被苍生。但我们仔细看看卡拉瓦乔这幅作品中的圣母,凌乱的头发,白得像纸一般的脸,还有臃肿的腹部,这明显就是一具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尸体。据说,卡拉瓦乔是以溺水身亡的妇女为模特而塑造的这一形象。这种从极度真实中显现出的平凡“人性”,更能将围绕在圣母周围那些因失去圣母而陷入极度悲痛的门徒们的绝望烘托得淋漓尽致,也更能打动普通人的心。但这种人性至上的手法显然已经盖过了“神性”,所以被教会拒收也是意料之中的。 我们再看此画的构图,从画面的左上方,一缕温暖的光线划破幽暗的背景从天而降,照在玛利亚身上。这种构图法是卡拉瓦乔所惯用的明暗对照法,通过加深画面阴暗的局部,用一束明亮的光线穿过主要呈现的对象,从而将形象的物理真实和观众的心理真实感大大提升。通过比较文艺复兴时期达芬奇、米开朗基罗、拉斐尔等人的作品就能明显看出,这种手法虽非卡拉瓦乔首创,但在文艺复兴时期的其他画家那儿却是不多见的。 接下来,让我们再看另一件名为《圣特雷萨的沉迷》的雕塑作品,是出自巴洛克时期另一位鼎鼎大名的艺术大师贝尼尼之手。这件作品是他在一六四五年所创,描绘了修女圣特雷萨在幻觉中见到天使降临的情景。这里需要解释一下,圣特雷萨是十六世纪西班牙的一名修女,由于她天生就有癫痫的痼疾,一到发病时就失魂落魄,眼前出现各种幻境,亦能看到种种神迹。艺术家贝尼尼清晰准确地抓住了修女在病发时异于常人的精神特质,呈现出当天使的剑即将刺进她心窝的那一刻脸上纠结的表情,将心中对上帝之爱的极度狂喜与对死亡将至的极度恐惧相交织的那一种凌乱纠结的情感表现得出神入化,淋漓尽致。相较之前不同时期的作品,这种以强烈扭曲的面部表情来展现人内心欲望的手法是没有的。这正是巴洛克时期的艺术家们通过不同于文艺复兴含蓄内敛的艺术表现,而是以另一种更加强烈且动人心魄的方式来呼应这份人文主义情怀的尝试,因而独具内涵。 关于巴洛克时期的审美标准,从当时的贵族阶层(尤其是妇女)的服饰装扮中便能窥见一二。夸张的卷发,精美的珠宝配饰,短俏的波浪状上衣在缀满蕾丝花边的哥特式袖领的衬托下更显娇娆华贵。而下半身宽大又不乏流动性的裙摆,在纤细的束腰下如花朵般绽放。巴洛克时期追求的就是这种宏大、夸张、精美夺目的视觉效果,并反应在当时生活的方方面面。如在雕塑方面,多用圆形、椭圆形、梅花形等不规则形状,在装饰上也非常强调曲线动态。位于梵蒂冈东面的圣彼得广场和教堂就是伟大艺术家贝尼尼所设计的。环形廊道上布满高大的圆柱,其间又有不少形态各异的雕塑以作点缀,既体现了那个时代讲求气派的特点,又展现出罗马教廷的威严。 我们可以从这一时期很多的雕塑作品中看出,不管是人物衣服上多变的褶皱,还是人身体刻意扭曲所形成的螺旋状姿态,亦或是人物脸上夸张丰富的表情都是巴洛克时期审美观念的切实体现。在文艺复兴向巴洛克过度之间,有一种被称为“Mannerism”(这里可译作“矫饰主义”)的流派被看作是巴洛克这种风格形成的重要因素。这种崇尚豪华,极度追求夸张激烈的艺术形式虽然在某种程度上确实略显浮夸,但却能更细腻地表现出人物情感,更贴切地去体现那以人为本的“人文主义”情怀。 谈到巴洛克,相信大多数热爱音乐的朋友第一个想到的应该就是大名鼎鼎的乐圣“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西方音乐史将巴洛克与古典主义时期的分界线划定为一七五零年,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巴赫这位划时代的大师就是在这一年与世长辞的。一代大师的陨落造成了一个时代的终结,可想而知,西方音乐在巴洛克时代占有何等重要的位置。现在,就让我们来详细看看巴洛克时期的音乐又是怎样的一番风貌吧。 一七四六年,法国哲学家普鲁赫(Noel—Antoine Pluche)首次使用“巴洛克”一词来讽刺当时一位小提琴家竭尽卖弄的炫技演奏。后来,他又进而将当时在法国和意大利流行的音乐分为旋律丰富自然、和谐优美的“歌唱性音乐”与新奇大胆、快速喧闹的“巴洛克音乐”两类。而当时的法国思想家与文学家卢梭在他的《音乐辞典》中对巴洛克音乐的定义也是偏向于贬义的,他认为这种类型的音乐“和声混乱,充满着不协和音,且旋律刺耳不自然,音调难听,节拍僵硬。” 而实际上,巴洛克音乐同样继承了文艺复兴的核心精神——以情感为中心的理念,并且与当时的造型艺术间存在着一定的联系。这是一种宏观热情,充满着活力的艺术,同时在细节上又非常注重装饰性,强调情感的表现与戏剧性的对比。故而,在整个巴洛克时期,很多从事音乐创作和理论研究的学者都非常关注如何让音乐打动人心这个美学问题,由此形成了一种“情感论”(Affektenlehre)的音乐理论。这一理论的形成,源自当时人们对古希腊学术的广泛兴趣。亚里士多德在《修辞学》中提出了人类既抽象又理性化的情感是的的确确存在的,认为一个优秀的演说家应当准确地把握和唤起听众心中的这些情愫。因此,巴洛克的音乐家们也想用自己创造的音乐来准确传达出歌词中所表达的情感内涵。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巴洛克式的情感表达和后来的浪漫主义的情感表现是不一样的。巴洛克作曲家们所表现的情感并不是自己个人的情感,而是一种理性化、类型化的人类共有的基本情感,和浪漫派的那种激情澎湃相比,它更像是一种相对静止的情感。故而言知,巴洛克的作曲家们在表现各种情感时,并不依赖自己的独创性,而是会用一套当时约定俗成的音乐表现手法,以特定的、字典式的音乐模式去表达特定的情感。这种模式化的手法被称作“音型”(figures)。例如,一串急促的音符,一段装饰性的华彩,或是几个特定的和声,不同的节奏型和织体的变化都能象征和暗示某种固定对应的情感,这也是为什么巴洛克音乐总能给人一种那个时期的固有印象之原因了。 细聊巴洛克音乐,就一定绕不开意大利著名作曲家克劳迪奥·蒙特威尔弟了,这是一位承前启后的伟大音乐家。在他一六零五年出版的第五卷《牧歌集》的前言里所提出的“两种实践”,成为之后整个巴洛克时期音乐创作并行不悖的规范和雏形。 蒙特威尔弟所指的“第一实践”,是指以帕莱斯特里那的音乐风格为代表的十六世纪的作曲规则,这些法国尼德兰复调传统的既定规则已在扎利诺的理论著作《协和的体制》一书中被定型和总结,被人们称作“古老风格”。这种风格以文艺复兴时期的无伴奏合唱为代表,是一种延续文艺复兴时代复调传统手法的创作规范。作曲家在采用此种“实践”创作时,需时刻注意对位写作的优美,在使用不协和音时应非常慎重,如对二度、七度等音程的使用是要严加限制的,和声的结构(这里指复调音乐)成了压倒一切的首要因素。 而接下来的“第二实践”则是蒙特威尔第在意大利牧歌创作中形成的另一个写作规范。采用“第二实践”进行创作的作曲家们应当将如何有效地表达歌词的意义和情感放在第一位,即和声应为表现歌词而服务。因此在这一实践中,歌词是最重要的,和声的作用退居次位。随着文艺复兴而兴起的“人文主义”对音乐最大的影响就是使音乐与文学的联系更加紧密,诗人们更加注重诗歌的音响,而作曲家们则着意去模仿这一音响。正因如此,巴洛克作曲家们为了扩展音乐的表现力,使音乐能更好地为表现歌词服务,对一些旧的对位规范和限制进行了大胆的突破。对于一些明显偏离了对位法则的做法,他们亦看作是合理的。此外,这种以表达歌词为主,和声映衬为辅的做法实际上就是一种不同于复调织体的主调和声手法,也就是说,它基本上是由旋律加和声伴奏的形式构成。 “第二实践”脱胎于蒙特威尔第对意大利牧歌的创作,他的牧歌创作历程体现了十六世纪末十七世纪初牧歌风格的急剧变化。在他牧歌集的前四卷中,主调和复调风格相互结合,不仅观照了对词意的表达,也考虑到了音乐作品的整体性和戏剧性。但在他的第五卷牧歌中,宣叙性的旋律风格已经凸显在主流的地位,第七卷则多半都是带伴奏的独唱、二重唱、三重唱等。 十六世纪的意大利牧歌是文艺复兴时期极为重要的世俗音乐体裁,歌词多为单段,韵律自由,以各种诗歌类型为创作素材,如十四行诗、巴拉塔、坎佐纳、抒情或叙事的八行诗等。 牧歌所选的诗作大多具有丰富细腻的情感内涵,常借景抒情,寓情于景。而在创作手法上,既有简洁明朗的主调风格,又有模仿的复调元素,不同手法的选择皆根据表达歌词的需要而定。 这种牧歌体裁形成于十五世纪意大利北部的一种以表现爱情和讽刺为主的“佛罗托拉”(frottola),这是一种主调织体的世俗音乐体裁。此外,牧歌的产生与发展还与文学诗歌领域的彼得拉克运动有着密切的关系。 牧歌的发展自然受到了当时两种不同观念的支配,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发展方向。第一种观点坚持认为,牧歌的音乐应以传达歌词意境为主,故而早期的牧歌为四声部,多采用主调织体,作曲家常以高音声部的旋律来清晰表达歌词中的朴素情谊。而另一种观点则认为,牧歌中所选用的诗歌是如此的高雅不俗,作曲家应该创作出和这些高雅诗歌相匹配的精致音乐。为此,必须调动一切创作手法,尤其是先人在复调音乐中所积累起来的丰富经验。 所以,纵观巴洛克时期的音乐,它是处在复调织体和主调织体这两种“实践”并行不悖,又相辅相成的一个状态。我们可以从巴洛克时期对管风琴的改良中看出,这一时期的管风琴除了音色更加统一,而且能让任何一个复调声部的线条在需要突出的时候显得更加清晰明亮。也就是说,巴洛克时期的管风琴已经成为了一种既适合弹复调音乐,又适合演奏主调音乐的乐器。 而在整个巴洛克时期,似乎带有主调倾向的“第二实践”更具代表性。为什么这么说呢?除了十六世纪在欧洲普遍流传的劳达赞歌(Lauda)、维拉内拉(Villanella)、小坎佐纳(Canzonetta)及芭蕾歌(Balletto)等主调风格明显的声乐体裁外,巴洛克时期最重要的一种音乐形式“通奏低音”就是最好的证明。 “通奏低音”是巴洛克时期一种典型的音乐形式,是一种主调和声的织体,由旋律加和声伴奏构成。它以低音声部和高音声部这两条基本旋律线为作品结构的主要框架,一条是贯穿整个作品的持续低音“通奏低音声部”,而另一条在其上方的高音声部则以华丽,富于装饰性著称。在实际创作中,作曲家只写出这两条主要声部,而中间的和声则省略不写,由演奏者用键盘乐器或其他可以演奏和弦的乐器(如鲁特琴等)即兴奏出。为了提示演奏者,作曲家常会在低音声部的上、下方或旁边标记出相应的阿拉伯数字,这些数字提示着低音与上方声部之间所应构成的音程关系。 为了方便理解,我就以现代和声代号为例来加以简单解释。请看下面这三组和弦: 假设回到通奏低音的写法,应该就是这样: 第一组C和弦根音上方的Mi和So被下面的数字3和5取代了。3代表根音上方的三度音(即Mi),而5则代表距离根音应该有五度音程(也就是So)。后面两组和弦的3、6与4、6都是这个道理。而在实际的写谱中,诸如C和弦这样的正常大三和弦一般都会省略不写,而像C/E这样以三度、六度关系构成的和弦一般会只写一个6,只有像第三组C/G这样包含了特殊纯四度音程关系的和弦才会将数字关系全部写出。 除此之外,如果低音标记的数字是4—3,则意味着低音上方的四度音作为延留音或是倚音,需要解决到三度音;而如果标记数字为0,则说明演奏者只需要演奏低音即可。另外,数字旁边的升降号则表示需要使用变化音。 通奏低音的起源可以追溯至十六世纪末教堂音乐中的管风琴低音声部。到十七世纪以后,作曲家们才开始写作更为独立的低音线条。第一个提出通奏低音概念的是维亚达纳(Ludovico Grossi da Viadana),在他一六零二年的《100首教堂协奏曲》的前言中声称,自己是通奏低音的发明者。 通奏低音了贯穿整个巴洛克时期,成为巴洛克音乐的一个最重要也普遍被作曲家们广泛应用的一种技术特征。因此,有学者索性将巴洛克时期称之为“通奏低音时期”或者“数字低音时期”。由于通奏低音的运用,必定促成和声体系的进一步发展,以调性取代中古时期的调式是巴洛克音乐的又一个重要特点。 从中世纪延续下来的教会调式主要以音符的排列(也就是音列)来表现曲调的性格色彩,不同调式具有不同的特点。如亚里士多德认为利地亚调式(Lydian)使人悲伤庄重,多利亚(Dorian)表现出温和稳健的性格,而弗里几亚调式(Phrygian)则可以激发人们心中的激情。这是一种音符横向发展的表现方式。而巴洛克时期以三和弦为基础的调性写作,以各大小调的和声色彩(而非调式色彩)来表达乐思,和弦是由音符纵向排列构成的,对之后调性音乐的发展起着深远的影响。 我们现在所熟知的大小调体系是从文艺复兴时教会调式中孕育而来的,而真正形成一个成熟的调性体系则是在巴洛克中期完成的。十七世纪中叶,器乐音乐的发展以意大利北部的博洛尼亚乐派为代表。维塔利(Giovanni Battista Vitali,1632年—1692年)便是该乐派中承前启后的一位重要代表。他器乐创作的某些特点可以说为之后音乐语言的发展和提高奠定了一个坚实的基础。如,和弦与动机的模进产生乐句、功能性和声集中在主、属和弦的范畴、低音保持稳定的节拍,并在某些条件下承担起动机的角色。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大小调的调性和声系统已在他的创作中初步形成。 法国作曲家拉莫在一七二二年出版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音乐理论著作《和声学》中就首次对调性和声体系作出了详尽的论述,为和声学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而如今被我们所熟知的两套巴赫《十二平均律钢琴集》,在不同音高的大小调上进行音乐创作,就是这种调性和声在实践方面的成功运用。 由于和声学的高度发展,当时不少作曲家将“第一常规”的复调创作手法纳入到了主调功能和声体系中,从而形成了一种被和声主宰的新的对位方式,被称作“调性对位”。其实,早在十七世纪中期,在和维塔利同属博洛尼亚乐派的另一位杰出作曲家科雷利(Arcangelo Corelli,1653年—1713年)的创作中,其调性特征更为清晰明确,调式的痕迹已然无存。他似乎成为西方音乐史上第一个完全运用大小调体系来创作的作曲家。在他的每一首作品中,都包含着主调与复调的风格。他的对位即是以和声为基础,被调性所节制的一种对位。因此,说巴洛克音乐是由“第二实践”中的主调和声体系所主宰的一种音乐也不为过。 此外,巴洛克时期在声乐方面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声乐从教会中走出,朝着更加世俗化的方向发展。新生的歌剧(Opera)成为那个时代最大规模的音乐体裁,并对欧洲音乐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相比之下,我们中国的戏曲艺术早在十三世纪便已经产生了,而欧洲的歌剧却足足迟来了四百年之久,一直到十七世纪前后才出现在意大利的佛罗伦萨(由佩里、卡契尼作曲,利努契尼写脚本的《尤里迪西》)。因此,歌剧的诞生被认为是巴洛克初期的一件大事。 在器乐方面,从中世纪起,器乐音乐就被禁止涉入教会(管风琴除外)。所以,它只能在世俗民间流传,且作为声乐或舞蹈伴奏的附属品其独奏水平非常有限,一直停留在比较原始的地步。另外,由于那个时代的器乐演奏大多都是即兴的,所以很少有乐谱流传下来。即使有个别的谱例保存至今,却也很难准确读懂。因此,我们很难对中世纪器乐音乐的真实面貌有一个很清晰的认识和梳理。而从文艺复兴开始,器乐音乐渐渐有所发展,并开始有了独立于声乐之外的趋向。如利切卡尔(Ricercare)和幻想曲(Fantasia)这两种非常相似的半即兴性的乐曲就是十六世纪出现的不依赖于声乐形式或舞蹈节奏的独立的器乐体裁,一般由鲁特琴或键盘乐器演奏。而到了巴洛克时期,器乐则彻底从声乐中得到解脱,地位更加独立。很多作曲家都纷纷为特定的乐器写作大量的新曲目,纯器乐体裁得到了相当的发展。前面所提到的模式化、类型化的巴洛克式音乐语言也融入到了器乐作品中,形成了一些独立的特点。在这样的背景下,最具代表性的器乐体裁协奏曲(Concerto)孕育而生了。这种音乐体裁脱胎于文艺复兴中晚期的协唱与合唱。协奏曲以一件或多件独奏乐器与管弦乐队协同合作为基本构架,其中独奏器乐常以动人的华彩片段和精湛的演奏技巧为作品的点睛之笔。 在巴洛克早期,西方音乐总以意大利为中心。但到了晚期(也就是一六九零至一七五零年),音乐发展的中心开始向欧洲北部转移。这一时期也是巴洛克音乐最为完善,登峰造极的一个阶段。同年出生的巴洛克音乐巨匠巴赫、亨德尔、多米尼克·斯卡拉蒂,以及比以上三位稍微年长一些的拉莫更是共同携手为那个最为辉煌的时代画上了完美的句点。 学术界普遍认为,以“洛可可”(Rococo)风格的出现为巴洛克时代的终结,从而与接下来的新古典主义划清界限。很多艺术爱好者或许对“巴洛克”与“洛可可”两种风格没有一个具体的感受和认识,也不明白二者究竟有哪些具体差异。现在,我们就来简单地来聊聊这个问题。 洛可可作为巴洛克风格的尾声,自然具备和包含了很多巴洛克时期的审美元素。但巴洛克风格所讲究的恢弘、高大、气派等特点却被洛可可的玲珑纤巧、轻浮、繁复又罗曼蒂克等元素所取代。如果将巴洛克风格比作显示王权的威仪,那么洛可可则散发着纯情男女竭尽矫情的柔情呢喃。 从洛可可风格的装潢来看,在原本宏伟的巴洛克式建筑中增添了不少繁复却别具装饰性的元素,恰似女性身上堆叠的那些雍容复杂、珠光宝气的珠宝首饰。从线条上看,很少用到笔直的线条,而多用曲线,天花板和墙面有时以弧面相连,转角处配以缠绵难分的花花草草,这既是巴洛克风格的延续,又更显纤弱娇媚。在整体色调上,洛可可不再似巴洛克时期那样以强烈的色彩来展示大气磅礴,而是更显小家子气,常用简洁明快的色调为主(如粉红、玫瑰红等浅色系)。而从局部装饰上看,巴洛克时期无论是家具还是建筑,在设计上都包含着绘画、音乐、文学等门类的理念,极富人文内涵。而到了洛可可时,尤其喜爱用贝壳、旋涡和山石作为装饰的元素,颇有自然主义的倾向。为了刻意突显自然性,洛可可风格有时甚至不注重对称,形式富于变化。 笔者认为,洛可可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女性的审美视角发展而来的一种风尚,原因有二。 第一,从它的兴起来看。法王路易十四劳民伤财建造了庞大奢靡的凡尔赛宫,其政治寓意十分明显,就是要将法国各地的贵族阶层约束在自己的眼皮子底下,让他们早晚都来向自己请安。这样做,一来可以树立他作为太阳王的威严,二来则可以让这些有钱有势的皇亲贵族长期离开自己的封地,断了他们的谋反篡权之念,以巩固波旁王朝的统治。但到了其曾孙路易十五即位后,面对住在凡尔赛宫中一波又一波的长辈,有的甚至和他的太爷爷路易十四是一辈人,这些人不可能再像路易十四在位时那样每天早晚行君臣之礼。相反的,当新国王路易十五见到这些叔叔婶婶们时,倒是要规规矩矩地向他们行晚辈之礼。日子久了,路易十五便不胜其烦,于是下令将住在凡尔赛宫的亲戚们统统迁出,并把他们安顿在巴黎。就这样,这些离开了凡尔赛宫廷的贵族们便开始在巴黎近郊购置土地,修建私宅。以前住在凡尔赛宫的时候,大家低头不见抬头见,日子就算再无聊,拉拉家常、聊聊八卦一天时间也就这么打发过了。如今大家都分开四散了,衣食无忧的爵爷们便开始寻花问柳以填补精神上的空虚。所以,这个时期大到建筑小到器皿用具,多半还是延续了巴洛克的某些特点,但在装饰上却显得更为精致、轻巧,特别容易引起女性的好感或是吸引她们的注意。尤其是当时兴起的女性沙龙,更将这种审美风向推到了极致。 从另一方面来讲,洛可可是由法王路易十五的情妇蓬巴杜侯爵杜夫人引领出来一段风尚。 蓬巴杜夫人虽为国王的情妇,但在史学家的眼中,她是一位拥着着极高品味的艺术赞助者以及极有政治野心的女政治家,与后来路易十五的另一位著名情妇杜巴丽夫人相比,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在蓬巴杜夫人的慷慨赞助下,法国艺术在各领域蓬勃发展,一些后世极富名望的文学家、艺术家都受过她的恩惠(如伏尔泰、孟德斯鸠,宫廷画家让·马克·纳蒂埃等)。她曾积极组织修建各种有利于艺术繁荣的公共建筑,也常热心参与各种艺术活动。如一七五二年,围绕作曲家佩尔格莱西洛可可风格的趣歌剧《女仆作夫人》而爆发的一场“法国派”与“意大利派”的激烈论战,蓬巴杜夫人就领着自己的情夫国王路易十五站到了法国派这边,而王后却选择支持意大利派。在政治方面,蓬巴杜长袖善舞,甚至直接左右到了路易十五对一些重要国事的决断。如当时由奥地利王位继承而引发的七年战争,路易十五听信了蓬巴杜夫人的建议,与哈布森堡家族联盟,将整个法国投入到了这场残酷的战争之中。战争在整个欧洲,乃至世界各地广大的殖民地间展开。而对于作战计划,路易十五亦对这位闺中的女诸葛言听计从。故而战斗在前线的很多法国将领经常收到一些用眉笔画出的作战图,这毫无疑问便是蓬巴杜夫人的杰作了。 由此可知,由一个极富品味的女性引领出的一种潮流又怎么能不具备女性审美的情趣呢?而这种风格在音乐领域的体现包含在史学家所概括的“前古典主义”风格中。也就是说,“洛可可”(Rococo)、“华丽风格”(Gallant Style)与“情感风格”(Empfindsamkeit)这些处于巴洛克尾声的艺术风格共同勾勒出了十八世纪中叶欧洲音乐的大体风貌。所以,无论是在上面提到过的法国音乐家拉莫的作品中,还是在巴洛克晚期巴赫与亨德尔两位大师的一部分作品或片段章节中,乃至后来古典主义时期海顿和莫扎特一些轻松愉悦的作品中都能感受到那种高雅、灵动,极富装饰性的洛可可式的痕迹。 洛可可正如它的名字一样(Rococo,既指巴洛克的瓦解和颓废之意)已经完全执着于形式,成为一具内涵干瘪的华丽外壳。这也标志着以文艺复兴开始的具有人文主义觉醒意识的时代,在经历了极富戏剧性又画龙点睛的巴洛克转折后已经走到了尽头。可博大的人文主义情怀却并没有因为一个时代的终结而被历史所埋没,它仍在延续,且越来越深入人心。这也为欧洲艺术史的不断向前发展提供了强大的资本和源源不断的动力。
|